![Symphonies nos. 1, 2, 5 & 7 / [music by] Jean Sibelius ; directed by Humphrey Burton.](https://serv.npac-ntch.org/DVD/6B/DV06944.jpg)
伯恩斯坦名作精選 第2輯, Disc 1 (藍光版)
- 題名: Symphonies nos. 1, 2, 5 & 7 / [music by] Jean Sibelius ; directed by Humphrey Burton.
- 作者: Sibelius, Jean, 1865-1957. composer.
- 其他作者:
- Bernstein, Leonard, 1918-1990. conductor.
- Burton, Humphrey, 1931- cinematographer.
- McClure, John, 1929-2014. producer.
- Kühle, Gerdi editor of moving image work.
- Bense, Greta editor of moving image work
- Hohlfeld, Horant H., 1938- producer.
- Kraut, Harry J. producer.
- Sibelius, Jean, 1865-1957. Symphonies, no. 1, op. 39, E minor
- Sibelius, Jean, 1865-1957. Symphonies, no. 2, op. 43, D major
- Sibelius, Jean, 1865-1957. Symphonies, no. 5, op. 82, E♭ major
- Sibelius, Jean, 1865-1957. Symphonies, no. 7, op. 105, C major
- Wiener Philharmoniker performer.
- Unitel Film- und Fernsehproduktionsgesellschaft mbH. production company.
- Video Music Productions. production company.
- 其他題名:
- Symphonies.
- Leonard Bernstein, Wiener Philharmonic, Sibelius
- Leonard Bernstein conducts Sibelius
- 伯恩斯坦名作精選 第2輯, Disc 1 (藍光版)
- 西貝流士 第1號交響曲, 作品39
- 西貝流士 第2號交響曲, 作品43
- 西貝流士 第5號交響曲, 作品82
- 西貝流士 第7號交響曲, 作品105
- 出版: Berlin : C Major Entertainment GmbH ©2010
- 主題: Symphonies.
- URL:
https://serv.npac-ntch.org/DVD/6B/DV06944.htm
- 一般註:DV06944 為藍光版 Blu-ray disc ; 1080i ; 16:9 (symphonies nos. 1, 5, 7) / 4:3 (symphony no. 2) Program notes in German by Harald Reiter,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by Stewart Spenser and French translation by Odile Demange included in container. A production of Unitel GmbH & Co. KG, Munich, in cooperation with Video Music Productions, Inc., New York.
- 製作群註:Video director: Humphrey Burton ; audio producer: John McClure ; film editors: Gerdi Kühle, Greta Bense ; executive producers: Horant H. Hohlfeld, Harry Kraut.
- 演出者註:Wiener Philharmoniker ; Leonard Bernstein, conductor.
- 適用對象註:Wiener Philharmoniker ; Leonard Bernstein, conductor.
-
讀者標籤:
- 系統號: 005149366 | 機讀編目格式
館藏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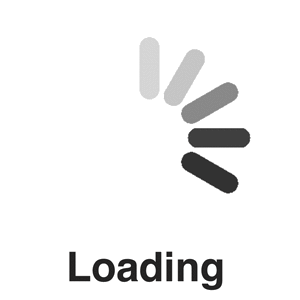
摘自 MUZIK雜誌 網站 : 伯恩斯坦,音樂中的愛與熱情 / 2018-09 Vol. 134 / 德岡直樹 連士堯 : 紐約愛樂的樂團首席,曾說過這樣的「證言」:「我永遠不會忘記,樂團巡演時演出的馬勒第1號交響曲《巨人》。那趟旅程很辛苦,常常到晚上10點半還無法吃晚餐。不過,每晚在雷尼(編註:伯恩斯坦暱稱為「雷尼」)指揮下的《巨人》,是首讓人想要永遠、永遠延續的樂曲。」
雷納德.伯恩斯坦的魅力在此一覽無遺。在一般優秀指揮能達到的成果之外,伯恩斯坦更可以帶出樂團團員的最高士氣,並完全沉浸在音樂演奏之中。簡單來說,就是「熱情.沉浸.投入」。與20 世紀後半葉受歡迎度平分秋色的卡拉揚相比,兩者音樂感與音樂表現截然不同。
舉例來說,鋼琴家齊瑪曼(Krystian Zimerman)在回憶與伯恩斯坦合作其第2號交響曲《焦慮年代》時曾說道:「那天晚上,伯恩斯坦來到我的後台休息室說:『25年前的這個夜晚,甘迺迪被暗殺了。啊!真是令人感到難過。』登台之後他開始指揮《焦慮年代》,意外地是,速度比我們彩排時還要慢上一倍,我覺得這是直截了當地反映出他心底情感的悸動。他就是位這麼誠實的音樂家。」
類似這樣的故事,我們很少在卡拉揚身上聽到。這並不存在著「好壞」的問題,但在卡拉揚的指揮裡,很少展露出詮釋者當下的感情變化。卡拉揚詮釋最顯著的特性就是「完成度」,因偶然起意、有感而發等狀況,進而在演奏速度跟詮釋上有具體改變,此點卡拉揚應該是「希望完全避開」的吧?這也可以直接聯想到,UNITEL 公司在1970 年代大量錄製音樂會影片時,卡拉揚對於攝影彩排跟影像剪輯的執著十分出名,而伯恩斯坦和維也納愛樂則可以直接採用音樂會現場轉播的影片,以製作角度來看,伯恩斯坦的方式有效率多了。
伯恩斯坦與樂團的練習情況,留下為數不少的影像,供現代樂迷驗證。不論誰來看,一定都會覺得伯恩斯坦就是不折不扣地「喜歡音樂」,他在自身完全沉浸於樂曲、勾勒出作品魅力的同時,還會揮汗努力,讓樂團徹底展現自己的音樂共感。
當中又以指揮、指導學生樂團的伯恩斯坦,令人特別感到有趣。為了毫不保留地讓學生理解音樂的美好,伯恩斯坦會請樂團成員一個一個說出自己追求的目標與熱情何在。而善用比喻、妙語如珠的伯恩斯坦,排練中也有許多趣事。就像阿巴多(Claudio Abbado)與青年管弦樂團建立的美好關係般,伯恩斯坦也是十分熱心地指導後輩。而在紐約舉行的「年輕人音樂會」(Young People's Concerts)系列,如此針對年輕觀眾的大規模啟蒙場次,更能讓伯恩斯坦完美發揮長才,這也算是他跟卡拉揚的不同點吧。其實伯恩斯坦自己曾如此說道:
「教學一事,對身為指揮家的我來說,是最根本的責任。在音樂裡知曉、感受的事情,我會全盤說出。我與樂團皆會盡力讓觀眾感受、知曉與理解。對我而言,指揮的真正樂趣,就是我們都在強行展現出『生命力』。這種感覺跟戀愛也十分雷同。」
伯恩斯坦的指揮技術也相當特別,相較其他人,他的揮棒方式較為簡單,但也可以說伯恩斯坦是「用全身在指揮」,以接近舞蹈的表現方式,讓樂團完全火熱起來。不只是在指揮台上用力跳起,直到現在,還是流傳許多他指揮法的軼事。
1969 年5 月,伯恩斯坦辭去紐約愛樂音樂總監一職,最後一場音樂會演出的是馬勒第3 號交響曲。雖說辭任理由是「想專心作曲」,但離職數天後,伯恩斯坦到了維也納,在維也納國立歌劇院創立100 週年紀念音樂會上指揮貝多芬的《莊嚴彌撒》。當時,伯恩斯坦還只被視為是個「美國樂團的指揮家」,唱片在歐洲的銷量也不算太多。希望進軍歐洲的伯恩斯坦,將自身目標設定為同樣身兼指揮家與作曲家的馬勒,並前往孕育馬勒的維也納。
比起紐約時期的錄音,伯恩斯坦在維也納、羅馬等歐洲城市的相同曲目演出,節奏明顯放慢許多,詮釋表現多偏向飽滿厚實,當中也有變得稍顯「誇張」的表現欲。之後幾年─特別是在DG 開始出版其錄音後,大家對伯恩斯坦的詮釋就開始分為「喜歡/討厭」兩派,而且不只是在聆聽的樂迷之間,樂團團員也是如此。與英國BBC 交響樂團排練時,伯恩斯坦明明身為1980 年代後地位不可動搖的巨匠,卻受到樂團團員的無情反對聲浪;另一方面,維也納愛樂則對伯恩斯坦表示:「我們完全能感受到他對音樂的愛與熱情。他能夠自由表現出自身所有情感,並擁有面對改變的勇氣。」維也納愛樂算是歐洲圈中較為保守的樂團,卻以演奏完美回應了伯恩斯坦的領導與熱情,兩者在DG 留下不少錄音。
從伯恩斯坦與維也納愛樂合作馬勒第5 號交響曲的練習場景裡,可看到幾乎能說是由伯恩斯坦編曲的馬勒詮釋:包括速度設定、節奏表現,甚至伯恩斯坦自己還唱出每個「彈性速度」,鉅細靡遺地說明,並且完全以這些指示帶領樂團。伯恩斯坦的馬勒詮釋無疑地很有魅力,但如果有所謂的「正統馬勒詮釋」的話,伯恩斯坦可以被視為是正統嗎?柏林愛樂的首位日本指揮家近衛秀麿,1920 年代時就在柏林等歐洲境內聽了包括克倫培勒、福特萬格勒、華爾特等人指揮的馬勒,他曾回憶道:「馬勒可說是典型的猶太人音樂,這裡也是、那裡也是⋯⋯追求完全徹底的表現。在那個時代,馬勒的音樂產生了小小的『熱潮』。」當中又特別強調克倫培勒的馬勒詮釋聽起來令人「難受」,留下了深刻印象。與這比起來,伯恩斯坦的馬勒,可說是完美雕琢的精品。
用這個觀點對應伯恩斯坦的詮釋,他的馬勒擁有繁複的變化、極為濃厚扎實,又有可以被形容為「誇張」的戲劇性,這可說是正統的馬勒演奏樣式嗎?我們沒辦法聽到馬勒自己指揮的演奏,現存資料裡,只有馬勒親手演奏的自動鋼琴留下來的記錄。身為維也納國立歌劇院音樂總監的馬勒,指揮過許多歌劇演出,雖然在自動鋼琴留下的是為自己創作歌曲的鋼琴伴奏記錄,還是可供後人考察馬勒指揮歌劇時的樣貌。
這種方式聽到的馬勒鋼琴演奏,事實上帶有輕快與彈性的節奏感,會令預設其「沈重、濃厚」的我們大吃一驚。現今的知名聲樂家,大概也很難與這份伴奏合作。當時的呼吸方式、樂句結構與現在都大相逕庭。
當然你也可以說,演奏風格不同,節奏感也會不一樣,但這不僅僅是速度的問題。速度與節奏感的關係不是連動的,「速度快」與「節奏感好」完全是兩回事,最好的例證就像是克納佩茲布許與克倫培勒常採用較慢的速度,好讓聲樂家容易演唱,但聽者並不會感到他們的音樂停滯不前。若我們聆聽華爾特、克倫培勒、波丹斯基(Arthur Bodanzky)等馬勒嫡傳弟子的演出(特別是歌劇)的話,會感受到馬勒的演奏應該不是屬於莊嚴或內斂氣質,反而更有可能是輕快又充滿朝氣。若聽了當時維也納宮廷歌劇院的聲樂家錄音,會發現他們的歌唱風格和戰後的「大型歌劇」(Grand Opera)完全不同,我們現在聽那個時代的錄音,往往會給出「老派、輕盈、快速」的結論。不過話說回來,將黏膩圓滑奏與美妙音色擺在優先順位的現代演奏方式,才是失去了原本的舒暢節奏感。
用這角度來看待伯恩斯坦的詮釋,說不定與馬勒本身的目標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吧。但這樣的馬勒詮釋,現今得到了很多樂迷支持,伯恩斯坦將自身的表現欲寄於音樂中,強化了壯麗的音樂效果,事實上也成就了令人感動的演出,DG 系列中的第3、第7 與第9號都是極為傑出的詮釋。1979 年10 月,在伯恩斯坦僅此一次客席柏林愛樂的演出,表現出的演奏緊張度以及面臨崩壞邊緣的樂團危機感,造成聽眾極度興奮的效果,備受世間好評。然而,如果講究整體平衡性與伯恩斯坦理念的貫徹度,1985 年與阿姆斯特丹皇家大會堂的版本,無疑更加優秀。關於客席柏林愛樂一事,一直以來坊間八卦不斷,伯恩斯坦雖然在少數訪問中提到此事,但他本人的說法也是稍顯誇大。
根據當時擔任卡拉揚助理指揮的高關健先生回憶,此演出實際情況是「原本預定4 次的彩排,的確少了1 次,但樂團的反應十分良好,伯恩斯坦看起來也是樂在其中。排練情況如同與維也納愛樂合作第5 號交響曲的錄影一樣,伯恩斯坦會一一詳細解釋他想要的快慢跟彈性速度,因此第一天還練不到第一樂章的一半,排練時間也延長了15 分鐘,第二天則延長30分鐘,第三天更延長了1 小時,而為了要彌補取消的那次排練,演出當天相當急促地決定要做公開彩排,開放給學生參加,但伯恩斯坦還是不滿意,公開彩排後又以『複習.溫習』的名義再度排練,才成就了這次的第9 號。此演出有諸多評論,但就像當時的定音鼓團員塔里臣(Werner Thärichen)、單簧管團員萊斯特(Karl Leister)所說,是一次親臨現場時,會感動到身體不禁顫抖的名演。」(引自與德岡的私人對話),至於伯恩斯坦所說的「他們用盡所有方式讓我的音樂會徒勞無功。」實在是過度被害妄想了。
現在終於要來探討這個問題:進入晚年後,與「有彈性」跟「輕快感」越來越搭不上邊的伯恩斯坦,該怎麼去定義他的馬勒詮釋呢?或更極致地說,伯恩斯坦晚年的演出漸漸被形容是「不管什麼樣的曲子,『伯恩斯坦風』的詮釋,皆會變成馬勒式聲響。」
這樣的看法,在1981 年指揮法國國家管弦樂團的法朗克D 小調交響曲,以及與維也納愛樂合作的西貝流士第2 號交響曲等錄音中落實,兩者皆是擁有巨大熱情與魄力的演出,如果真的在這樣的現場,我自己一定也會大聲拍手叫好吧!個人是相當喜愛此版法朗克。不過對真心喜愛西貝流士的聽眾來說,大概會覺得此版第2 號,有點過度詮釋西貝流士的美感了。這當然是一份令人感動的演出,不過在伯恩斯坦的詮釋裡,這份西貝流士也太過「伯恩斯坦風」了點⋯⋯。
日本樂迷傾向用「具精神層面」的評語來形容速度較慢的演奏。音樂的「精神」究竟是指什麼呢,雖然無法明確定義,但常說的「精神性」一般是指速度較慢、擁有宗教般莊嚴感的演出。若以這個定義,伯恩斯坦晚年的演出明顯是「精神性」大增吧。不過實際聽起來,在音樂表現的深刻化之外,為了能把自我思想最極限地放在每一個音符中,在旋律歌唱性的迴轉與節奏的自由運用上,伯恩斯坦的詮釋或多或少會變得有點「四不像」。(譯註:原文為「グロテスク」,為grotesque 之音譯,西洋穴怪圖像,指西洋傳統壁畫裝飾中會出現的人獸或動物與植物的混雜圖像。
例如1987 年伯恩斯坦與紐約愛樂的柴科夫斯基《悲愴》交響曲,長達17 分鐘的第四樂章引發熱議(卡拉揚的最後一次錄音是9 分43 秒,以速度緩慢聞名的傑利畢達克也只花了13 分鐘),其實在1986 年7 月,伯恩斯坦於檀格塢音樂節指揮波士頓交響樂團的現場,此樂章也花了14 分鐘左右。在這個其他人不會採用的極慢速度裡,從樂團的細微聲響中吐露出「悲愴」之魂⋯⋯可以讓人聽見如此效果。貫徹此速度的確帶來高度說服力,但也有地方被犧牲了吧。儘管如此,使用此表現力來詮釋馬勒時,明顯地能夠展現出演奏魄力。據說伯恩斯坦本人曾「教」維也納愛樂演奏馬勒,他本人說「在我演奏之前,維也納愛樂連一頁馬勒都演不好,教導維也納愛樂如何演出馬勒的就是我本人。」這真是事實嗎?其實在戰後到1960 年代,克倫培勒、華爾特、庫貝利克、米特羅普洛斯(Dimitris Mitropoulos)都曾與維也納愛樂演出過馬勒交響曲,管弦樂歌曲也有克利普斯、克勞斯、福特萬格勒等人的合作。1960 年代最具里程碑性質的維也納愛樂馬勒演出,正是1965 年在薩爾茲堡音樂節由阿巴多指揮的第2 號《復活》。因此,伯恩斯坦在維也納愛樂最重要的貢獻,應該是將此團介紹給美國,並且帶領維也納國家歌劇院進行成功的美國首演(1979)等成就,演出馬勒曲目只是象徵性地包含其中。後世評論時還請不要誤解。
另一個需要特別談論的主題,就是伯恩斯坦也會演奏鋼琴跟作曲,而且質量兼具,需要另外專文論述。從拉威爾鋼琴協奏曲、蓋希文《藍色狂想曲》到貝多芬跟莫札特的鋼琴協奏曲,皆是伯恩斯坦的鋼琴演奏曲目。作曲則是以三首交響曲為首,外加音樂劇《西城故事》、輕歌劇《憨第德》、歌劇《沉默之地》等,範疇極廣。一言以蔽之,伯恩斯坦在音樂活動上的最大特徵,不外乎就是極致表現出超越種類的強烈「音樂愛」。來自烏克蘭移民的猶太裔家庭、於美國出生的伯恩斯坦,在此地土生土長、學習茁壯,可說是「美國夢」壓倒性成功的展現。因此,據說伯恩斯坦去世後,送葬隊伍抬棺行進時,不斷聽到紐約市民在旁呼喊「再見了,雷尼!」(Good bye, Lenny!)
內容註
Symphony no. 1 in E minor, op. 39 -- Symphony no. 2 in D major, op. 43 -- Symphony no. 5 in E flat major, op. 82 -- Symphony no. 7 in C major, op. 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