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ll Strauss program全區
- 題名: All Strauss program / Produktion, Wilfried Scheib ; Fernseh Regie, Hermann Lanske ; produced by Austr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ORF.
- 其他作者:
- Österreichischer Rundfunk production company.
- Wiener Philharmoniker performer.
- Video Artists International film distributor.
- Scheib, Wilfried. television producer.
- Lanske, Hermann, 1927- television director.
- Magaloff, Nikita, 1912-1992. performer.
- Böhm, Karl, 1894-1981. conductor.
- Boskovsky, Willi, 1909-1991. performer.
- Altman, Allan. video producer.
- Strauss, Richard, 1864-1949. Burlesque, piano, orchestra, TrV 145, D minor
- Strauss, Richard, 1864-1949. Heldenleben
- 出版: Pleasantville, NY : Video Artists International ©2013
- 主題: Symphonic poems. , Piano with orchestra.
- URL:
https://serv.npac-ntch.org/DVD/5A/DV05230.htm
- 一般註:全區 ; 4:3 ; 黑白 The 1st and 3rd works are symphonic poems. Title from menu. Originally produced in 1963.
- 製作群註:Produced for DVD by Allan Altman.
- 演出者註:Nikita Magaloff, piano (2nd work) ; Wiener Philharmoniker ; Karl Böhm, conductor.
-
讀者標籤:
- 系統號: 005124256 | 機讀編目格式
館藏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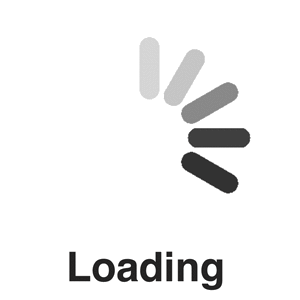
摘自 moonlike - Thema & Variationen 網站
Karl Böhm - Erzähltes Leben — 貝姆口述自傳 / hannyi
在Graz的早年
人到了某個年齡之後,就可以大致上論斷他的一生是否活得有價值,以音樂的術語來講,就是他對自己的人生,是否有一個正確的詮釋、是否有一個完美的演出。現在的我,差不多已經到了這種年齡了。我深信,一個藝術家的榮耀,非來自於任何頭銜。若我能具備某種值得世人尊敬的特質,而使貝姆這個名字成為某種典範之代名詞,這才是一個藝術家所能得到的最高殊榮。
根據我母親日記的記載:襁褓中的我,呀呀而出的第一個字是 “min” ,這個字所指的就是「音樂」。當時,每天早上11點,我總會聽到軍樂隊在行軍時的演奏。
父親是一位律師,有著一口美妙的男中音嗓音,他是Graz歌劇院的法律顧問。我開始學習鋼琴時,特別受到了Franz Weiss的指導。他是Graz歌劇院的豎琴手,也因此我能跟隨著他參加所有《玫瑰騎士》的採排。當時,那presentation of the Silver Rose的樂音,一直縈繞在我的心頭。
我很清楚地知道,我想成為一個音樂家。所以在1913年,我開始向Eusebius Mandyczewski學習和聲學、對位法與作曲。Eusebius Mandyczewski當時是維也納Gesellschaft der Musikfreunde的檔案管理者,他是布拉姆斯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我從他那兒看到了許多這位偉大作曲家的手稿。
初次登臺指揮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很快我被軍隊徵召。在軍中,我是一個優異的騎士,以當時的情況,我很有希望會建立起一番偉大的勳業。但因為一場我從馬背上摔了下來的意外,為這段未竟全功的潛在勳業,提前劃上了句點。
在1916年我成為了Graz歌劇院的提詞員。在我到劇院的第二天,有一場Aida的幕後橋段需要指揮,於是我客串上場了。可是當時的我,並不清楚如何比劃4/4拍子,亂比的結果引發嚴重的抗議,使我幾乎被轟下指揮臺。但我很快就學會了,也開始指揮輕歌劇。我記得一個趣事:有次某個女歌手想要降三音來演唱,可是樂團中的音樂家堅持只能降一個音。結果在演出八到十個小節以後,我們彼此的調才終於對了起來。這實在是很恐怖。我還聽到有觀眾說道:「難道說共產主義們也在歌劇院裡面暴動了嗎?」不久我開始指揮歌劇,如Victor Ernst Nessler的Der Trompeter von Säckingen與韋伯(Weber)的Der Freischütz。在此同時,我仍然在進行著我的法學博士學程。
很快地開始了我第一場的華格納歌劇演出,演出的是《羅恩格林》。當時Karl Muck也在聽眾席,他是非常著名的一位前輩級的拜魯特指揮家。他告訴我:「雖然你所演出的Bridal Chorus像是一場polka,但可以看出你有天分。我願意帶你走一遍華格納的總譜。」從他那裡,我學到了許多的華格納演出傳統。接著,在貝多芬年(1920),我負責上演全新製作的《費德里奧》,隨後獲選為歌劇院的首席指揮,並且演出了很多場的音樂會與所有的歌劇。其中,也包括了我心愛的《崔斯坦與依索德》。
Munich, Darmstadt與Alban Berg
不久,華爾特(Bruno Walter)邀請我去慕尼黑指揮歌劇。我接受了這家國立歌劇院的任職。在我們一起共事的那些日子裡,我從他的身上學到很大的成長。
在慕尼黑度過六個成功的寒暑之後,我到了Darmstadt指揮。在那兒我遇到了兩位先生:一位是劇院的監督Carl Ebert,以及時任經理的Rudolf Bing。Rudolf Bing後來成為紐約大都會劇院總經理。當時我們一起上演最新的現代音樂製作,包括亨德密特(Hindemith)的Neues vom Tage、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當時所有的歌劇、以及貝爾格(Alban Berg)最新的(但不是最後的)歌劇—《伍采克》(Wozzeck)。貝爾格人性的特質,與他優異的音樂天賦相稱。我只能在世界各地首演這部作品,作為我對他情誼的回報。我把這部作品帶到了薩爾斯堡、維也納、納普勒斯(Naples)、布宜諾賽利斯(Buenos Aires)、以及大都會。在納普勒斯我們排練了超過三十次以上,在布宜諾賽利斯更引起轟動,連續兩個樂季的票都搶購一空。
離開Darmstadt之後,我前往漢堡(Hamburg)工作,在那兒我遇到了理查史特勞斯,當時我正在上演他的歌劇Arabella。與這位天才的相遇改變了我的一生。
Dresden, Richard Strauss與Mozart
自1934年起的九年間,我成為德勒斯登(Dresden)歌劇院的指揮。在我第一次排練時,那兒的音樂家們跟我說:「幸好我們至少不用再學習如何對話了。」因為Ernst von Schuch也是Graz人,他是我前幾任的前輩,是個優秀的音樂家。在德勒斯登,我為兩部史特勞斯的歌劇舉行世界首演:《沈默的女人》(Die Schweigsame Frau)與《達芬妮》(Daphne)。其中《達芬尼》是史特勞斯提贈給我的。我常常與史特勞斯一同散步,一邊散步、一邊閒聊莫札特。史特勞斯是敬愛莫札特的。有一次他對我說:「你記不記得《唐喬凡尼》第一幕終曲前,有兩小節慢版?我願意用我三部歌劇,來交換這兩個小節!」
他說這個橋段是從一個純粹歡愉的小步舞曲,轉折到深具悲劇性格的三重唱,而這麼戲劇性的轉折,竟然用兩個小節就完成了。這是莫札特無可比擬之天才的一個例證。
另外有一次他告訴我:「莫札特他能創作無止境般綿長的旋律。看看凱魯碧諾(Cherubino)的第二詠歎調,整個旋律一直綿延到詠歎調終止才結束。我很不幸的只能創造有限長度的旋律,但對這些旋律,我做了一切作曲家所能做的工作。」
身兼作曲家與指揮家的Strauss
史特勞斯也是個指揮專家。在莫札特與他自己的作品方面,他是個無可比擬的詮釋者。我記得有一次,在他排練Elektra時,他放下指揮棒,說:「各位,今天晚上請大家安靜地演奏。這個作品寫得實在太吵了。」從史特勞斯與Muck那兒,我學到了小動作的原則。他們兩人都對此抱持著相似的態度:「打拍子的右手,只是要告訴大家說『我們現在進行到這裡。』如此而已。除此之外,真正帶領樂曲的是大家的精神的力量。」這是說指揮者應當以總譜為標準,扮演中介者的角色,將總譜的理念投射到那些在他四周的演奏者身上。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實上身為一個藝術工作者,指揮家很少對他的工作成果滿意——通常他對樂團、以及指揮樂團的自己,都抱有恨鐵不成鋼的心理。
有一次,一位攝影師要求史特勞斯做出在指揮時高舉雙手的動作。史特勞斯一口回絕,說道:「我曾經講過,指揮的時候左手最好什麼都不要做,現在你竟然想強迫我做出使用左手這種事情!不。我要把左手插在褲子的口袋裡。」然後有一次他指揮《沒有影子的女人》,在進行到最後一幕四分之一的高潮處,他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演出結束之後,他問我對於這場演出有沒有什麼想法,我說:「很好。不過我想到史特勞斯博士曾經講過的:指揮家在演出時絕對不應該從座椅上站起來,而且也絕不應該揚起他的左手;這兩項你今天都做了。」史特勞斯喃喃自語了幾聲,就把話題帶開了。四天之後他又指揮了同一部作品,在同一個高潮處,我看見他又作勢準備要站起來了,但最後他壓制了自己,並用左手緊抓著桌子。接著他向我的包廂招了招手,這個小動作一方面展現了他的自我控制力,也顯現了他的幽默感。有一次,他微笑道:「我在指揮時絕不流汗,汗流浹背是觀眾的事。」
有一天,我在史特勞斯Garmisch的家中作客,《達芬妮》的作詞者Joseph Gregor也在座。Gregor在樓上的房間裡面作詞,每寫完一頁,稿件就在我們間傳閱,最後才遞到史特勞斯的手上。史特勞斯旋即在其上註明,應採何種旋律、何種調性。我常常感到自己跟不上他的創作速度。另外一次,他一面從草稿中謄抄校正本的總譜,同時又跟我聊著莫札特。我覺得這樣不妥,說你不能一面作曲,又同時分心聊其他東西。他回應道:「繼續聊啦,親愛的貝姆,這是我唯一放下工作的時刻啊。否則創作會一直在我腦海中自動進行著。」有一次他實在生氣了,說:「有人說我是個被遺棄在過去的人。可是,看看Elektra裡面Klytemnestra那一段,有誰能找出比這段更現代的作品!」
就像所有偉大的作曲家一樣,史特勞斯早期也受到其他人的影響,作品中出現了前人的影子,特別是華格納。但是到了《狄爾惡作劇》的時候,他已經從別人的影響下走出來了。他的作品之所以好聽,不單單是因為他的配器成功,這只是原因之一;但他那典範一般的旋律對位技法、以及對於曲式展現令人難以置信敏銳度,這才是更主要的原因。在這點上,他與莫札特展現了相似的特質。
在史特勞斯去世的12個小時前,他曾經突然地清醒過來,並對我說了一段話。他說如果上帝再次賦予他一次全新的生命,他還是會做與此生同樣的事。
在維也納短暫的插曲
在德勒斯登的那段日子,令人感到非常滿意,特別是那異常傑出的合奏效果。在那兒,我們總輕易就做出能令別的劇院感到妒忌的效果。我相信如果今日的人們能花心思去探索,他們還是可以做出以前我們劇院那般的優異合奏。
由於我曾經在維也納演出,特別是曾與愛樂共演過許多音樂會,維也納國家歌劇院(Wiener Staatsoper)邀請我接任他們的總監職務。我在1943年的1月1日到職,上演華格納的《名歌手》(Die Meistersinger)。在1944年,所有的歌劇院都被勒令關閉了。我不希望我們歌劇院的伙伴們淪落到軍火工廠工作,所以採用了音樂會的形式,來上演莫札特與華格納的歌劇作品。這樣是一個很奇妙的體驗:儘管上半場的華格納《女武神》第一幕也很適合音樂會形式演出,但是總感受到舞台的必要性;然而上演《費加洛》或《女人皆如此》的節選本時,卻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缺陷感。不管有沒有舞台背景,音樂都同樣地活靈活現、栩栩如生。
莫札特的天才
我深深愛著莫札特。但是我很晚才接觸他的音樂,這是受了我父親他們的影響。父親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華格納主義者,他們一貫的論調是:「為什麼莫札特的音樂聽起來都一樣,簡直就像是同一首一直在反覆一般。」直後後來,我才了解這種「反覆」的必要性。
我一直在探索,如何才能做出保證一流的莫札特詮釋。我得到了一個結論:莫札特他能用音樂來表達人類所有的情感,可是他從未露出過於感傷的多愁善感。所以我總是避免著用感傷的手法來詮釋莫札特。我曾反覆琢磨他展現的天才,最後使我相信:他是造物主所創造的一個完美個體,打從他呱呱墜地之際,就已經是個完美的存在。這種完美的存在,並不屬於這個世界。人們很難解釋:一個和弦,某些作曲家用起來顯的平凡無奇;何以一旦落入莫札特手中,立時展現奇蹟般美妙的效果,猶似上帝賜與之恩典?曾經有個朋友問他是如何作曲的,他回答:「很簡單啊,只要我有時間,我就能作曲了。曲子都在我的頭腦裡面,早就已經完成了,只是我得簡單整理一下就好了。」只有舒伯特(Franz Schubert)的創作力能與他相比。舒伯特也是能在一年內,寫出幾百首不朽歌曲的偉大作曲家。
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的毀滅與重生
在12.3.45那天,這個數字,彷彿代表命中註定似的,維也納國家歌劇院被炸毀了。很多維也納人和我一樣,只能在焦黑的廢墟之前,悄然站立。
在回到Graz一段時間之後,我開始旅行演奏,並開始建立我的國際性事業。後來奧地利政府邀請我接手國家歌劇院的重建工作,我很高興地接受了,在1955年11月,我指揮了《費德里奧》。雖然那時我的國際性旅行演奏已經增加了。
我父親是Egerland人,我母親是亞爾薩斯(Alsace)人。我在老式的奧地利傳統文化中成長,現在人們所期盼的是文明之間的對話,當我在指揮莫札特以及史特勞斯之時,聽眾應該可以聽到那來自古老的奧地利傳統的聲音。
內容註
Tod und Verklärung : op. 24 (24:44) -- Burleske for piano and orchestra (19:37) -- Ein Heldenleben : op. 40 (Willi Boskovsky, violin solo) (42:00) / Richard Strau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