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列頓 魂斷威尼斯 - 歌劇
- 題名: Death in Venice / the Glynedebourne Touring Opera production ; by Benjamin Britten ; libretto by Myfanwy Piper after the novella by Thomas Mann ; a BBC TV production in association with RM Arts ; stage directors, Stephen Lawless, Martha Clarke ; directed for video by Robin Lough.
- 作者: Britten, Benjamin, 1913-1976.
- 其他作者:
- Tear, Robert, 1939-2011.
- Chance, Michael, 1955-
- Opie, Alan, 1945-
- Piper, Myfanwy, 1911-1997.
- Jenkins, Graeme, 1958-
- Mann, Thomas, 1875-1955. Tod in Venedig
- London Sinfonietta.
- Glyndebourne Festival Chorus.
-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Television Service
- RM Arts (Firm)
- Glyndebourne Touring Opera.
- 其他題名:
- 布列頓 魂斷威尼斯 - 歌劇
- 出版: [Germany] : Arthaus Musik 2006, ©1990.
- 主題: Operas. , Operas--Film adaptations.
- URL:
https://serv.npac-ntch.org/DVD/6A/DV06307.htm
- 一般註:4:3 ; 英德法西文字幕 ; 2, 5區碼 Originally produced in 1990. Special feature: Trailer.
- 演出者註:Robert Tear, Alan Opie, Michael Chance ; Glyndebourne Chorus ; London Sinfonietta, conductor, Graeme Jenkins.
-
讀者標籤:
- 系統號: 005140013 | 機讀編目格式
館藏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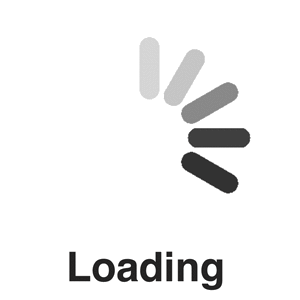
摘自 alpha追逐的蹤跡 網站
布列頓的歌劇大全集 (12): 魂斷威尼斯 Death in Venice
《魂斷威尼斯》是布列頓最後一部歌劇作品,也是布列頓十二部歌劇作品中,人物最單純,卻最具張力及深度的作品(個人意見,僅供參考)。這部歌劇可以說是布列頓獻給皮爾斯的最後作品,隨著布列頓健康狀況日盆惡化,他隨時準備寫他的最後一部作品。皮爾斯這位跟他一起生活數十年的朋友,在當年尚難容許同性戀的社會下,始終能不計毀譽一起走到生命盡頭,布列頓當然要為他留下些紀念。於是《魂斷威尼斯》就成了皮爾斯個人秀,加上故事本身就是描述一段奇特又激烈的情感,不免又要投射到布列頓對同性戀的一些看法了。
提到《魂斷威尼斯》,不免要提到維斯康提(Visconti)的同名電影,他們都是根據湯瑪斯.曼(Thomas Mann)的原著改編,正巧布列頓的歌劇是在維斯康提的電影推出後才完成,加上維斯康提的電影大受歡迎(連帶的使馬勒第五號交響曲的慢板樂章廣受喜愛!),因此有人認為布列頓必是因著電影的關係而寫成歌劇。關於這點,布列頓十分不悅,首先他指出他研究這部作品已經五、六年了,而且在1971年的春天已進行到第一幕的部份,維斯康提的電影在1971年初上演,由此可證布列頓並非受維斯康提的刺激;再者,布列頓根本沒去看維斯康提的電影,兩者根本沒有關連。
布列頓的身體狀況在1970年後轉壞,他的醫生診斷是心臟冠狀動脈的問題,要求在1972年秋天開始治療。此時布列頓正在進行《魂斷威尼斯》,他知道這次大手術可能會影響到未來的創作,因此他要求醫生將手術時間延後,一直到他完成這部歌劇後再進行。布列頓告訴他的朋友:「我必須在任何狀況發生前努力完成這部作品,一則因為它可能是皮爾斯最後的主要歌劇角色;二則因為這是一部我想了很久的歌劇,不可再延了!」布列頓奮力在1973年初完成譜曲,越到後面他越急切,他原先尚希望有機會親自指揮首演,甚至錄音,但能在手術前完成已屬大幸。1973年五月,布列頓終於進了開刀房,手術沒失敗,但也不完全成功,布列頓的右手再也無法彈鋼琴了。
皮爾斯知道《魂斷威尼斯》對布列頓的重要性,他解釋道:「對他而言,這部歌劇多少總結了他的感受,甚至包含他孩提時代的回憶……在劇終,阿森巴赫(Aschenbach)自問他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麼?知識?還是失去的天真?難道追求美麗、愛情,就必會導致混亂嗎?全是布列頓自己不斷在問自己的問題。」對於一位藝術家,又是同性戀者而言,布列頓的心情必定受到劇中人阿森巴赫的深刻感染。原著作者湯瑪斯·曼應該不是同性戀者,他帶著太太及小孩造訪威尼斯,這是一個令他驚豔的城市。而阿森巴赫的經歷,卻是一次真實的經驗。
如果要我選出那個歐洲城市最迷人,我會選威尼斯,她是我到目前為止最懷念的地方,我是在若干年前的三月間到達威尼斯的,她沒有巴黎的浮華,也沒有維也納的人文,她只是個漂在水上的古城。可能是因為沒有車輛奔馳,也沒燈紅酒綠,這個城市散發出一股神祕安祥又迷人的味道,有錢的人租艘著名的搖船(Gondola),穿梭在大小水道間;沒錢的人,可以搭公共汽船,從麗都(Lido)遊到聖馬可士廣場,或用走的也很愜意。威尼斯是很公平的,有錢跟沒錢的享受一樣多。想著威尼斯,卻又不敢想很快再去一趟,總覺得原來留下的印象太美了,怕被破壞。再去一次巴黎,可以多邊一個美術館,再去一次紐約,可以多看一場歌劇,但是再去一次威尼斯,可以多得到什麼?所以上次只到了米蘭,也許還沒準備好要用什麼心情再訪威尼斯吧!
歷年來,文人雅士都對威尼斯有所著墨,尼采就會說過:「假如要找一個音樂的同義字,我會說是威尼斯。對我而言,音樂就是淚水,淚水般的音樂,我也知道要我回憶起南方的這地方而不顫動是很難的。」本劇的原作者湯瑪斯·曼也有同樣的感受:「對某些人,威尼斯這個名字與一股特殊的憂鬱相連……我心必將悸動,假如我再到這裡一次。」就是這種幽幽暗暗的情境,使人的心情特別容易受到感染,想必阿森巴赫就是在這種心情下,而對劇中男孩產生那種奇特的愛慕。在阿爾卑斯山南方的這個城市,有著北方人所嚮往的解脫,北方的日耳曼民族嚴肅且有紀律,但太過拘謹克制;南方的民族熱情大方,大而化之。一座阿爾卑斯山脈斷出了兩種不同的民族性格,阿森巴赫的北方性格,在南方獲得了徹底的解放,雖然也解放了他的生命。
「海」則是布列頓選擇威尼斯的另一主要原因,布列頓的主要歌劇都跟「海」脫不了關係。《彼得‧格萊姆》及《比利·巴德》的主角都葬身海中,而阿森巴郝望著小男孩走向大海,自己則病死於面對海洋的窗前,三者差別不是很大。布列頓對大海有著深刻的依戀,也許在他心目中,「海」是可以躲避及遠離塵囂的唯一去處,是一處可以避開人們閒言閒語的寧靜地。「海」也是神祕不可測的象徽,一如在《仲夏夜之夢》中的森林,威尼斯是建築在海上的城市,除了主要河道稍寬外,大部份的河道只容兩艘搖船擦身而過,河道兩旁大多是四、五層高緊緊相連的樓房,兼有大海及森林的疏離輿神祕,她的確有著這麼一股令布列頓無所釋懷的悽美。
「海」同時也是混亂的象徵,潮來潮往,浪花四濺,有時風平浪靜,有時波濤洶湧。阿森巴赫在遇到小男孩後,突然發現了自己積壓多年的情感,也激發了他閉鎖多年的靈感,可是他又面臨了道德的抉擇,雖然發現了多年來追求的理想,卻又有一股強大莫名的阻力命他無法前進。幾次他都欲言又止,幾次他都想離開卻又不忍,小男孩有意無意的注目,屢屢使他內心澎湃,甚至阿森巴赫自己都已吶喊出「我愛你!-l,彷彿海浪般的相互衝擊著,終被浪濤擊沈了。
就布列頓自己而言,五十多歲原本應離死亡的時間尚有一段距離,但顯然布列頓自知來日有限,選擇《魂斷威尼斯》可能跟他預知死亡無關,但音樂的寫作則深受影響,一方面是他為自己一生的創作做個總結,順便也融合他對印尼甘美隆音樂的理解,合成為布列頓式的甘美隆。另一方面,他加速完成本劇,企圖及時完成最重要的願望,然而劇情本身的激盪力也不斷在增強中,因而使本劇內聚力不斷提升,雖然沒像《比利,巴德》那般在未了給人的震撼,也足以令人反覆思索不已。
初看到阿森巴赫的反應時,我第一個聯想到的竟是巴兩托克的《奇異的滿州官吏》,那是一種急切且熾熱,而又不知所雲的情感,而死亡是結束這種情感的唯一方式。普契尼式的義大利歌劇,多的是一見鍾情的泡沫感情,雖很速食,倒也還算「正常」,像布列頓及巴爾托克這種神經質的情感,比較符合二十世紀的精神狀態。
「死」是否跟「海」一檬,都是逃避現實的地方,也都是很神祕的事情呢?有點太灰暗了。布列頓的阿森巴赫原本要離開威尼斯,回到冷酷現實的北方,然而瘟疫的消息促使他不顧危險留下,想要警告小男孩速速離開,他的死是自殺性的,其實無論是他一走了之,或是他送走小男孩,他都不可能再見到小男孩了,生命也就沒意義了。而巴爾托克的滿州官吏是陷入一種不可自拔的歇斯底里狀態,即使是別人的匕首刺進自己的胸膛,仍然無法轉移他的注意力,這是種狂熱。
海與死亡,畸情與死亡,海與畸情,這個三角關係,應該就是本劇的基礎了。
《魂斷威尼斯》仍再度由美芳維,派普女士擔任劇本編寫的工作,美芳維成了布列頓晚期的主要合作夥伴。本劇由貝福德(Steuart Bedford)於1973年六月十六日在艾德堡音樂節舉行首演,布列頓本人健康差到無法出席首演,只有在隔週收聽到廣播。九月十二日,布列頓總算在麥芽廳看到一場特別為他演出的《魂斷威尼斯》。
在此之後,布列頓仍抱病作了些曲子,同時因為他無法再替皮爾斯伴奏,還找了位年輕的美國鋼琴家培萊亞(Murray Perahia,現在很紅!)來當他的伴奏。布列頓在這個時期最著名的作品,就是他為珍娜·貝克寫的《Phaedra》(收錄於Decca布列頓歌劇系列的《強暴路克雷夏》中)。同時,在1976年二月,他的第一部歌劇《保羅‧邦揚》總算首次在歐洲的廣播中出現,連布列頓都忍不住流下淚來,沒想到郡部作品那麼強而有力,他自己都快忘光了。
1976年六月十二日,布列頓獲英女王封為「貴族」( Peerage),可以入座女王身旁,等位比Sir還高,布列頓並不接受其他封爵,但此次特別的封位,命他深覺尊榮而接受,只是他並沒有機會真的去王宮與女王同座就是了。
1976年夏天,他仍到北歐去渡個假。他最後一部尚未完成的作品是清唱劇《讚美我們偉大的人們(Praise We Great Men)》。1976年的十一月四日,布列頓死於皮爾斯的懷裡,才過完生日十二天,享年六十三歲。
英國作曲家提佩特在布列頓的追悼廣播中提到,布列頓在《彼得·格萊姆》成功後,「希望自己立定志向,成為二十世紀的專業歌劇作曲者。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然而在未來的音樂史中,他將永遠被提起,他確實做到了!」布列頓一生共作了十二部歌劇作品,最後以《魂斷威尼斯》為總結,不也很美嗎?!
本劇的確是布列頓自己的一個總結,而在布列頓親自督導下,由貝福德在1974年與首演人馬為Decca錄下全曲(425 669-2),皮爾斯在本劇中展現了獨撐大樑的氣勢,幾乎從頭唱到尾,他必須很含蓄的表達阿森巴赫的熱情及禁慾,這是他個人了不起的成就,也充分的顯示他對布列頓的了解。另一位量身訂作的是演唱多個角色(包括旅人、老船夫、經理、理髮師等)的John Shirley-Quirk,他也是布列頓的老班底,變換於各個角色中,毫不含糊。貝福德在布列頓的督導下,展現了布列頓風,是無可挑剔的權威。很可惜,本劇目前只發現這個版本,不知Virgin的希考克斯或Philips的柯林·戴維斯何時會錄到此劇,我睹他們會找在英國歌劇界執牛耳的Philip Langridge擔任主角。
摘要註
Describes the grandeur and shabbiness of Venice in the grip of disease. Portrays the moral and physical degeneration of Aschenbach, the writer whose obsessive and self-devouring pursuit of beauty in the form of the boy Tadzio leads him to humiliation and de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