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ano concerto in A minor, op. 54 ; Arabeske, op. 18 / [compact disc].](https://serv.npac-ntch.org/CD/3B/C003813.jpg)
舒曼 鋼琴協奏曲, 作品54
- 題名: Piano concerto in A minor, op. 54 ; Arabeske, op. 18 / [compact disc].
- 作者: Schumann, Robert, 1810-1856. composer
- 其他作者:
- Minneapolis Symphony Orchestra
-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 Janis, Byron, 1928-
- Skrowaczewski, Stanisław, 1923-2017.
- Menges, Herbert, 1902-1972.
- Schumann, Robert, 1810-1856. Concertos, piano, orchestra, op. 54, A minor
- Schumann, Robert, 1810-1856. Arabesques, piano, op. 18, C major
- Tchaikovsky, Peter Ilich, 1840-1893. Concertos, piano, orchestra, no. 1, op. 23, B♭ minor
- 其他題名:
- Concertos,
- Schumann & Tchaikovsky piano concertos.
- 舒曼 鋼琴協奏曲, 作品54.
- 舒曼 阿拉貝斯克, 作品18.
- 柴可夫斯基 第1號鋼琴協奏曲, 作品23.
- Mercury living presence : the collector's edition.
- 出版: E.U. : Decca 2011.
- 叢書名: Mercury living presence , Mercury living presence : the collector's edition. [1] ;26
- 主題: Concertos (Piano) , Piano music.
- URL:
https://serv.npac-ntch.org/CD/25A/C025146.htm
https://serv.npac-ntch.org/CD/3B/C003813.htm
- 一般註:Title on container spine: Schumann & Tchaikovsky piano concertos. "An original 35mm magnetic film recording"--Container. Durations: 30:00; 7:12; 33:00. Program notes by Jess T. Casey and John Scrymgeour (15 p. : port.) inserted in container.
- 演出者註:Byron Janis, piano ; Minneapolis Symphony Orchestra ; Stanisaw Skrowaczewski, conductor (1st work) ;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 Herbert Menges, conductor (3rd work).
-
讀者標籤:
- 系統號: 005038230 | 機讀編目格式
館藏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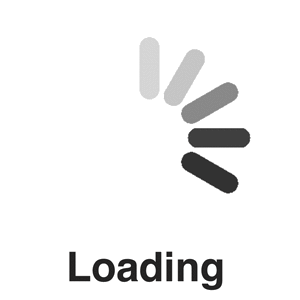
摘自 印象三重奏 網站
前兩年曾經有個機會在卡內基音樂廳聽過拜倫‧詹尼斯的現場獨奏會,功力相當深厚,他的蕭邦一直餘音繞樑,令人難以忘懷。他也是這回來幫費得曼教授擔任伴奏的Sara Beuchner的老師。
推薦這張大家都不陌生的曲目,相當動聽、精彩!
摘自 博客來音樂館 網站
1928年出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凱斯波特,七歲跟隨馬爾庫斯與列文涅夫婦學琴,1943年在法朗克.布拉克指揮下與 NBC交響樂團成功的演出拉赫曼尼諾夫第二號鋼琴協奏曲。霍洛維茲於1944年2月聽到堅尼斯再度與費城管弦樂團合作這首協奏曲後(指揮是十四歲的馬捷爾),立刻決定收堅尼斯為徒,展開為期三年的師徒關係。堅尼斯於1948年首次在卡內基音樂廳演出,1960與62年兩度到蘇聯巡迴,得到聽眾與樂評界一致的喜愛。堅尼斯於1967年在法國發現蕭邦兩首沒有被發現過的圓舞曲手稿;
1973年正值事業顛峰時期,堅尼斯卻因關節炎而被迫減少演出場次。堅尼斯以詮釋蕭邦、普羅高菲夫與拉赫曼尼諾夫的作品最受好評。鋼琴演奏之外,堅尼斯也是位作曲家,作品包括數首敘事曲與民歌等。
美國作曲家、鋼琴家、指揮家戈特沙爾克之後,有好長一段時間美國沒有誕生真正的偉大鋼琴家。美國當然產鋼琴家,可是他們的名聲卻被那些俄國和波蘭湧進來的外來移民所遮掩。其中包括安東.魯賓斯坦、阿圖.魯賓斯坦、加上拉赫曼尼諾夫、帕德雷夫斯基和霍夫曼。1928年,外來鋼琴家的陣容更因霍洛維茲來到美國而錦上添花。
二十年後,美國音樂圈終因兩位本土誕生的鋼琴奇才而活絡,其一是卡培爾,其二是堅尼斯。美國終於有了可供後進學習景仰的本土鋼琴家。堅尼斯的先祖是俄國移民,他以演奏李斯特和蕭邦著名,是戈特沙爾克音樂的傳揚者,也是霍洛維茲第一個學生。
堅尼斯1928年1月1日出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很早就被發現有音樂天份,七歲成為列文涅夫婦的學生。但一年後,頻繁的演奏讓列文涅夫婦無法定期授課,於是他們決定讓堅尼斯跟隨同事馬爾庫斯繼續學琴,列文涅夫人則每月檢查一次他的進度。堅尼斯九歲舉辦第一場獨奏會,十五歲(1943年)與 NBC交響樂團演出第一場協奏曲音樂會,曲目是拉赫曼尼諾夫第二號鋼琴協奏曲。次年,霍洛維茲在匹茲堡聽到這位十六歲鋼琴家的音樂會,即當時也是十多歲的馬捷爾。霍洛維茲很欣賞堅尼斯的才華,當下決定收堅尼斯為徒,展開為期三年的師徒關係。
馬爾庫斯女士對於失去愛徒並不高興,但是這位橫刀奪徒的鋼琴家是當代鋼琴泰斗時,她也莫可奈何,只能從旁警告和這麼一位性格強而複雜的音樂家相處得特別小心。「她真的很沮喪,」堅尼斯回憶道:「而她說的也沒有錯。她認為我走錯了路,而我也的確陷於困擾當中。」如同知名樂評家哈洛德.荀白克所說:「馬爾庫斯教堅尼斯冷靜處理音樂,現在霍洛維茲卻教他成為一個感性的名家型鋼琴家。」
無論如何,堅尼斯還是從霍洛維茲處學得許多無價之寶。霍洛維茲強調音色、踏板和自由的節奏感。「舞台上你得誇大一點,」霍洛維茲教他:「否則你的演奏就會變得不夠有趣。」堅尼斯受此影響,「我變得無法控制自己,在台上極度誇大。我是做過頭了。有趣的是,當他教我時,從來不曾為我示範過一個音符!但是我在課外倒是常聽他彈琴。我成為他家庭中的一員,他旅行時我必需跟著他以便定期受課。他在家裡會為我彈奏數小時的鋼琴,曲目跨及整個鋼琴曲目,所以儘管他從來不示範,但我還是從大量的聆聽中補償了這點。我完全明白他的處理方式、他對作品的看法……當時,我只有十七歲,我還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已經變成霍洛維茲的翻版!」
當霍洛維茲決定送堅尼斯上卡內基廳的時候,他自己也意會到此事的潛在危機。他一再向他的經紀人強調,堅尼斯演奏宣傳一概不准提堅尼斯是他的學生。「這樣會毀了你!」他向堅尼斯說:「你一定會被稱為『霍洛維茲第二』,而這絕不是你所想要的。」他又說:你一定會犯一些錯誤,而這些錯誤可是你自己的。」所幸當時堅尼斯的人格已經夠堅強,他的自我意志力掙脫了與霍洛維茲師生關係所帶來的包袱。1948年10月2日,堅尼斯終於在卡內基廳成功舉辦獨奏會,很顯然的,他沒有成為霍洛維茲的翻版。他和霍洛維茲都擔心的事終於安然過關。
演出後的樂評大都是高度贊揚。《紐約時報》道恩士(Olin Downes)如是說:「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聽過這麼充滿才氣的鋼琴家。堅尼斯同時兼備音樂性、感情、智慧和藝術氣質。」這個評論把堅尼斯捧上了天,而堅尼斯的藝術事也就像火箭一樣一飛衝天。數年後,堅尼斯談到總結他與霍洛維茲學琴的心得:「我從他那兒學到如何讓鋼琴歌唱,如何使用鋼琴的音色,如何讓鋼琴發揮它的最高性能。」
四年後,堅尼斯為RCA Victor錄下第一張獨奏唱片,其中不少收錄在這張唱片裡:李斯特、蕭邦和首次發表的舒爾茲-艾弗勒《美麗的藍色多瑙河》。要明瞭堅尼斯特殊之處,這些樂曲都是極好的例子。他有大膽、活潑和充滿音樂性的節奏性,似乎永無極限的技巧,以及把一部音樂演繹成獨一無二的天份。紐約重要樂評家之-湯姆遜(Virgil Thomson)也這麼評論:「堅尼斯是個極有能耐的鋼琴家,不管在技巧或氣質方面。」
雖然堅尼斯曲目跨及十九到二十世紀初:拉赫曼尼諾夫、普羅高菲夫和李斯特協奏曲,貝多芬和布拉姆斯的奏鳴曲、舒伯特和舒曼的作品,但他還是對蕭邦有著特殊的偏愛。除音樂本身外,堅尼斯本身的氣質恐怕比音樂本身更能表達「蕭邦」的特性。如同哈洛德.荀白克所描述:「在舞台上,堅尼斯瘦長、幾乎弱不禁風的樣子,幾乎馬上喚起台下女性觀眾的母性憐愛本能,就像蕭邦本人再現一樣。等到他彈完一首《夜曲》,半數觀眾都猜想會有位喬治桑從後台走出來,攙扶著他前往地中海靜養。」
堅尼斯形容他和蕭邦的關係為「靈魂交感」。堅尼斯闡述道:「蕭邦對他的弟子說過許多次『用你的靈魂去彈奏。』如果你想創造真正偉大的音樂,就必需得這麼做。如同現實生活,你付出愈多,得到的回饋也愈多。有人害怕無保留的付出,但是對我來說,只有全心付出才能喚起最高的美感和表現這個世界的神秘。讓靈魂充份歌唱是妙不可言的經驗。如果技巧真能和自己想像力結合,然後呢,神奇的事就會發生。你可以稱它為交感、出神入化、渾然物外……隨便你。反正它就是『音樂』,不再是鋼琴、也不再是音樂家;
此時音樂的境界早已超越這一切。」
堅尼斯相信他「確實和蕭邦有些奇妙的因緣,最早是1955年在諾昂特巧遇阿蘿蕾.桑(Aurore Lauth Sand),也就是喬治桑的孫女。接著是他發現了四份蕭邦從未發表過的手稿,然後又在法國電視台的電視節目中演出蕭邦這個角色。」如同霍洛維茲一樣,堅尼斯的特點在於優美的歌唱性。如同堅尼斯告訴學生:「你不是鋼琴家,而是位歌唱家。當然你學的是這種樂器,但你其實是同時扮演歌唱家和伴奏兩個角色。有很多年輕學覺得怯於去『唱』。以前蕭邦就建議他的學生,常去聽偉大聲樂家演唱,你就知道怎麼彈鋼琴。」
堅尼斯在七○年代確立了當代頂尖鋼琴家的地位,每樂季演出一百場左右。1952年與荷蘭阿姆斯特丹大會堂管弦樂團演出,成功的在歐洲首度亮相;
六○年代則在俄國贏得滿堂采,也成為與俄國樂團合作錄音的第一位美國鋼琴家。他錄製的普羅高菲夫第三號鋼琴協奏曲贏得法國唱片大獎,法國政府頒授給他騎士榮銜;
這個榮銜過去只有兩位美國人得到,其一是雕刻家考德爾,另一位則是小提琴家曼紐因。
十二年後,只有家人和少數朋友知道堅尼斯面臨巨大的痛苦與危機:他患了關節炎。堅尼斯嚐試精神療法和包括針灸在內的治療但沒有效果。他的演奏驟降到每季五十場,每次演奏愈來愈伴隨難忍的疼痛。有一陣子堅尼斯完全中斷演奏,情緒也跌到谷底。「這是個生或死的掙扎。音樂是我的生命,是我所有的世界。我無法當訴其他人我患了關節炎,我不要別人同情或建議,而我也不希望讓聽眾們抱怨我的演奏不完美。」堅尼斯終於在1985年打破沈默,在一次白宮音樂會中公開承認他的關節炎。「在那次宣言之後,」他回憶道:「我覺得兩肩負擔突然解放了。藏住一個秘密是多麼吃力的事!」從那次事件之後,他成為「國家關節炎基金會」的代言人,在美國各地為基金會舉辦籌募基金音樂會。「要學習如何與痛苦週旋」他說:「或者你只能過著被限制住的生活。我想告訴大家,如果我能,你也辦得到!」
摘自 SONY Music 網站
拜倫.堅尼斯(Byron Janis)是美國最傑出的鋼琴家,一生多次面臨逆境卻奮鬥不歇,無論琴藝或成就,都可名列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鋼琴大師之一。堅尼斯1928年出生於美國賓州,四歲開始學琴,十歲時左手被玻璃割傷而手指完全失去知覺,在多次手術與持續練習下,1944年堅尼斯首次演出拉赫曼尼諾夫第二號鋼琴協奏曲,不僅贏得眾人驚嘆,霍洛維茲更主動收他為第一個入門弟子。
在冷戰期間,堅尼斯與范克萊本成為美國人的超級偶像,堅尼斯的精湛琴藝更塑造出「美國的浪漫樂派」風格。然而當演奏事業攀至最顛峰,身體的病痛接踵而來,痛苦不堪的關節炎幾乎摧毀了堅尼斯,不得不發展出自己的演奏方式,直到1984年才公開病情。但堅尼斯的才氣與熱情,就如同另一位鋼琴大師吉爾利斯贊云:「他讓鋼琴唱歌」。
摘自 博客來音樂館 網站 Mercury 發燒天碟錄音的歷史
一九五○年錄音工業逐漸從「轉速之戰」中平復過來。當時 RCA Victor 的四十五轉唱片正與發明乙烯密紋唱片的哥倫比亞唱片公司 (Columbia Records) 在市場上競爭。更早的七十八轉唱片早巳被這些新技術迅速取代。然而這場競爭最後並沒有輸家:流行音樂單曲唱片採用了四十五轉的唱片速度,密紋唱片的則適合錄製時間較長的古典音樂。
但是一年前錄音磁帶的普及化,帶給錄音工業歷史性的突破。這種更方便經濟的新媒介使許多小廠牌可以參與競爭,打破了長久以來錄音事業被 RCA、哥倫比亞壟斷的局面。與設備笨重的七十八轉唱片相比,輕便的 Ampex 磁帶錄音器材使小規模公司可以攜往歐洲錄音,費用比在美國用舊設備錄音還便宜。而倫敦、維也納、札格雷、布拉格等城市,多得是歡迎這些小公司錄音的管弦樂團、室內樂團。 當時在美國大批冒出來的國外錄音,是間接由一九四八年「第二次派翠羅聯盟禁令」*造成;
因為該禁令不准聯盟成員在美國錄音。外國錄音的引進對美國而言並不全然是福音,因為其中很多都是演奏平庸,錄音技術泛泛的速成之作。同時,美國境內管弦作品的錄音減少,直接或間接造成了業界的「轉速」之戰和古典廠牌的急速增加。在這情形下,許多大型演奏團體,例如芝加哥交響樂團與唱片公司的專屬合約也就鬆弛下來。總部設在芝加哥的獨立廠牌 Mercury 唱片公司,也就在這個紛亂多變的時代,正武投入古典音樂唱片市場。 Mercury唱片公司是一九四五年由艾爾文.格林(1rving Green)創辦的,初期以出版流行音樂為主。著名的製作人有:米勒(Mitch Miller)、葛蘭茨 (Noman Granz) 以及哈默德 (John Hammond)。旗下著名藝人有佩吉(Patti Page)、戴蒙 (Vic Damone) 和林恩 (Frankie Laine)。其中林恩的暢銷單曲《That’s My Desire》是 Mercury 第一張銷量破百萬張的金唱片。
Mercury在一九四七年冒險投入古典市場。哈默德(也就是現任副總裁);
把他加盟 Mercury 前所製作的一批七十八轉唱片掛上 Mercury 的商標,其中包括史特拉汶斯基親自指揮錄製的「敦巴頓橡樹園」協奏曲。哈默德在一九四八年聘請錄音評論家霍爾 (David Hall) 出掌新設立的古典部門。他交給霍爾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把這批老錄音轉為LP密紋唱片。
同年,Mercury取得一批二次大戰前與大戰期間德國錄音的美國代理權。這些錄音大部份是從廣播側錄下來。一九五○年又取得俄國作曲家哈察都量小提琴協奏曲的世界首演錄音發行權。這場音樂會在俄國舉行,由當時已經傳奇色彩甚濃的小提琴家大衛.歐依斯特拉夫擔任獨奏。俄國方面使用的是早就被西方世界淘汰的次等錄音技術。錄音工程師羅伯特.法恩 (C. Robert Fine,大家習慣稱他為 Bob) 當時主持 Reeves Sound Studio,負責處理Mercury公司在紐約的錄音事宜。他被賦予挽救這張記錄歐依斯特拉夫藝術重要錄音的重任。結果他的努力不負眾望,成功的把這張唱片發行出去。該唱片得到的關注和市場反應,使 Mercury 大受鼓舞,乃決定繼續發展古典音樂業務。
隨著營運狀況愈來愈好,Mcrcury與法恩建立更長遠而密切的合作關係。他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八○年代初期,負責監督製作 Mercury 的流行音樂、爵士樂以及古典音樂的錄音。但是法恩從來不曾成為Mercury的編制內成員。法恩在五○年代初期離開 Reeves Sound Studio,自行籌組公司,從事電影、電視及其它相關業務,例如特殊產品的承製與新技術的研發。法恩是第一位使用德律風根 (Telefunken) U-47麥克風的工程師。這種真空管電容器麥克風在日後「Living Presence」錄音技術的建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U-47麥克風的高靈敏度以及寬廣的頻率響應帶給法恩相當深刻的印象,他認為德律風根U-47型麥克風能夠呈現他理想中的管弦樂音色。 來自密西西比的年輕管弦樂團行政人員威瑪.柯札特 (Wilma Cozart),也在一九五○年加入Mercury古典部的工作行列。柯札特有很強的曲目和藝術理念,並懷抱對音樂的熱愛來到紐約。根據她四○年代晚期在達拉斯交響樂團和明尼亞波利交響樂團的工作經驗,柯札特相當了解美國樂團的優點與弱點。她很快的提出建立一套管弦樂曲目的計劃,這份計劃不像其他美國獨立廠牌,只是聘請國外音樂家錄音,而是嚐試與優秀的本土指揮家、樂團簽約合作。
首先,柯札特在格林的協助下與芝加哥交響樂團進行接觸,這時的芝加哥交響樂團已不再是RCA的專屬樂團。隨後她到明尼亞波利市探訪,該市在美國音樂界居有中樞地位。然後她也注意到在新任指揮及管理階層的的領導下,底特律交響樂團已經逐漸恢復往日的雄風。一九五二年,伊士曼音樂院 (Eastman School of Music)理事長韓森 (Howard Hanson) 與 Mercury 簽下專屬合約,準備錄製美國作曲冢的作品。後來這項計劃也擴展到芬聶爾 (Frederick Fennell)與伊士曼管樂團 (Eastman Wind Ensemble) 系列錄音。 參與錄音的每個樂團行政單位、指揮以及團員都非常高興能夠錄製唱片。雖然每個樂團的合約內容不同,但是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財務風險由參與計劃的單位共同分攤,使這些大膽的錄音計劃得以實現。這種理念在當時頗為先進,為未來許多類似合同立下基礎。
與芝加哥交響樂團第一次合作時,法恩想出一個簡化的錄音方式:他打算用單一麥克風來錄製穆索斯基的「展覽會之畫」。錄音於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兩日在管弦樂廳 (Orchestra Hall) 進行,由庫貝力克擔任指揮。法恩在指揮台正上方二十五英尺左右懸掛一隻U-47型麥克風。這個位置是在樂團綵排時決定的,利用整首曲子最爆棚的段落調整錄音訊號大小。從頭到尾錄音的動態未經加工修飾,絕無灌水或壓縮,所以它的演奏效果可說忠實傳達了指揮心中要求的音色。
從「古墓」的輕柔到「基輔城門」的猛爆高潮,這次歷史性的錄音都充份表現了拉威爾多采多姿的管弦樂色彩。紐約時報最重要的樂評家塔伯曼 (Howard Taubman) 聽過這張錄音後說道:「令人覺得好像在現場聽活生生的音樂會 (Living Presence)。」Mercury對塔伯曼的反應非常興奮,他們節用了塔伯曼的用詞「Living Presence」作為新發行的「奧林匹亞系列」的副標。一時之間,Mercury不但為聲音的傳真重現開創新世紀,也得到樂評家、愛樂者以及音樂電台的一致喝采,成為發燒友心目中的最佳廠牌。Mercury用單隻麥克風收錄大型交響樂團的作法,確實風靡了一般大眾。依 Mercury 與芝加哥交響樂團簽訂的合約,更多錄音計劃續由庫貝力克和杜拉第擔任指揮。這兩位指揮家的成就使 Mercury 在古典音樂市場上的地位更加穩固。 Mercury接下來把注意力轉到明尼亞波利交響樂團,這也是一個未有錄音合約的樂團。兩位美國最受歡迎的指揮:奧曼第和密屈洛普羅斯在個別接掌費城管弦樂團及紐約愛樂之前,都曾經帶領過這個樂團。當時的新任樂團總監是活力充沛的杜拉第,他早年在布達佩斯擔任指揮時,與巴爾托克、高大宜的交情匪淺,因此他的「管弦樂協奏曲」以及「哈利.亞諾斯組曲」通常被視為最具權威的詮釋。擔任蒙地卡羅俄國芭蕾舞團首席指揮期間的經驗,使杜拉第長於史特拉汶斯基和柴可夫斯基的芭蕾作品:杜拉第曾首創用他們的作品原稿灌錄這些芭蕾舞劇的全曲。任職於達拉斯以及明尼亞波利交響樂團時,杜拉第廣邀美國現代作曲家發表創作,充實了美國的管弦樂曲目,其中有一部份曾在Mercury 錄製成唱片。
一九五二年,Mercury與底特律交響樂團以及新任總監帕瑞 (Paul Paray) 簽約。此舉令唱片界跌破眼鏡,因為當時底特律交響樂團的狀況已經跌到谷底。雖然新任法籍音樂總監帕瑞在美國藉藉無名,但是樂團仍積極重整、吸收優秀團員,擴編為一○四位團員,令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帕瑞為 Mercury 樂團補充了不少光釆非凡的法系曲目。他指揮底特律交響樂團在 Mercury 的第一張唱片,收錄了拉威爾「波麗露」與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西班牙隨想曲」,在帕瑞的指揮下,底特律樂團顯露如同托斯卡尼尼指揮般的嚴謹、精確以及敏感的音色,素質與巴黎音樂院訓練出來的音樂家們難分軒輊。
Mercury在-九五四年著手進行-項古典音樂唱片史上的空前大計劃:以柴可夫斯基的管弦樂原稿錄製「一八一二」序曲,曲中用上真正的教堂鐘聲、加農砲與一隊銅管槳隊。這項錄音計劃分在三個地方進行。管弦樂部份由杜拉第在「諾斯羅普廳」(Northrop Auditorium) 指揮明尼亞波利交響樂團錄製;
克里姆林宮的鐘聲在耶魯大學校園內的哈克奈斯紀念塔 (Harkness Memorial Tower) 仿製;
拿破崙時代所用的加農砲則在西點軍校錄音,最後再把分頭錄好的音效剪接到正式的母帶上。
這張錄音史的里程碑得到熱烈的回響,更加鞏固 Mercury 在音響技術界與廣大消費者心目中的地位。多年來,Mercury的「一八一二」成為全美音響製造商在音響大展中,展示新型喇叭、唱頭與擴大機性能的最佳示範片。甚至「紐約客」雜誌(New Yorker) 撰文介紹這張唱片時,也以「碰!」(Boom)為標題。 一九五八年,Mercury以立體聲重錄「一八一二」。演出陣容是上次的原班人馬,但是鐘聲改用紐約河岸教堂(Riverdide Church) 的洛克菲勒紀念鐘 (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 Carillon) 錄製,加農砲則仍在西點軍校錄製。
一九五五年起,Mercury進行全面的立體聲化。最初使用的是四分之一英寸雙軌 Ampex 器材,法恩根據電影音效的經驗,請 Ampex 製造了第一架特別規格的半英寸、三軌錄音機。這種設備非常適合錄製古典音樂,新產品的效果不但令人吃驚,也成為往後 Mercury Living Presence使用的標準器材。法恩仍在音響平衡點使用一隻麥克風,然後在兩側添加二隻麥克風。錄音時,法恩坐在音樂廳裡,柯札特在音控室內操控,兩人搭配著找出音像的焦點,用視覺來比方,每個麥克風就像投射一束光線,最後三束光線重疊把樂團照亮。最後一個步驟,就是把音樂收錄在半英寸三軌的 Ampex 錄音機上。
把三軌轉換為雙軌的修飾工作委給柯札特,她幾乎是全程參與整個錄音過程。這是一項極其精巧的任務,必須以技術保住原來三軌錄音所凝結的定位。確保各樂器定在原來的位置,不致從音場中「跑位」。柯札特與另一位母帶轉唱片的工程師皮羅斯 (George Piros) 還必須奮力克服一個困難,就是既要維持原音,又要維持唱針在唱片上的正常循軌狀態。這可不是件簡單的事,必須同時克服唱片內側循軌困難、刻片瑕疵與唱片材質可能造成的不可測影響。
一九五六年春,霍爾離開 Mercury 前往丹麥,稍後在林肯中心負責管理作曲家羅傑斯與漢默斯坦的音樂檔案。同年秋天,WOXR 錄音監督勞倫斯 (Harold Lawrence) 在同年秋天加入 Mercury 的工作陣容。 理論上,一些抽象實體,例如唱片廠牌,是不太可能有具有獨特精神的。但是 Mercury 以其一聽就可分辨的音質、獨樹一格的曲目、與音樂家的緊密關係,使其產品成為上述規律的例外。這點與公司精神的傳承、錄音技術的延續有關。Living Presence catalog 新產品可信賴的高品質,使 Mercury 公司成長為國際廠牌之一,並開創了更寬廣的商機,一九五六年夏天,Mercury錄音小組第一次遠赴英國與哈雷管弦樂團及倫敦交響樂團合作。這次合作最重要的部份,就是在 Mercury 的英國分公司協同下,由巴此羅里指揮哈雷管弦樂團,為佛漢威廉士第八號交響曲進行世界首次錄音。在倫敦方面,杜拉第為他與倫敦交響樂團的十年錄音計劃灌錄首張唱片。從一九五○年至六○年間,杜拉第被賦予重建倫敦交響樂團,使恢復英國最受歡迎錄音樂團地位的重任。 Mercury與倫敦交響樂團多半在倫敦郊區的華福德鎮 (Watford) 音樂廳錄音。這個音樂廳的空間非常寬敞,硬木地板的坐位也可以移動,非常適合 Living Presence使用。通常只有合唱團在舞台上,管弦樂團團員全部在地板上。正前上方掛有三隻麥克風。錄音監督及工程師可以依需要調整樂器的位置,三隻麥克風的高度和角度對於聲音的平衡度非常重要;
Mercury錄音小組利用繩索、棍棒以及滑輪來調整麥克風的最佳位置。由於麥克風的平衡點非常難找,柯札特在找到平衡點後,就畫出錄音配置圖,不但畫出麥克風的位置,連各樂器的位置與高度都詳加記錄,包括管樂手下方的平台高度。甚至必須指定在地板某些地方鋪設油布,以防產生不必要的諧振。 Mercury Living Presence 從五○年代初期就採用錄音專車進行非錄音室錄音,在美國本土或國外皆然。車上裝有錄音機、鑑聽喇叭、麥克風、擴大機、電纜等器材,無遠弗屆的到偏遠的教堂、音樂廳,甚至野外戰場錄音。這是 Living Presence 一貫傑出音效的保証。
Mercury的錄音室外錄音,充份顯示法恩和助理工程師艾佰倫茲(Robert Eberenz) 的才能。為使 Mercury Living Presence 無論在何處錄音均能夠保持一貫的水準,他們花了很大心血在錄音專車的設計、保養和擴充上。例如為了克服倫敦晚間的濕氣,裝麥克風的匣子必得保存在保溫箱裡,交流發電機則必須一直開著,以確保真空管的正常功能。在伊士曼劇院 (Eastman Theater) 錄音時,則必須從停放錄音車的車庫到音樂廳,牽上多條避免無線電波千擾的特殊管線。
一九五七年到六四年間,Living Presence在唱片目錄上有了戲劇性的擴充。Mercury在底特律增添兩個錄音場地。一個是回音相當強的舊管弦樂廳 (Old Orchestra Hall),另一個則是凱斯工業高中 (Cass Technical High School) 的禮堂。帕瑞曾經在這裡為 Mercury 錄製一系列暢銷片。前者已經經過兩次整修,目前是底特律交響樂團的駐地。Mercury 在羅徹斯特繼續進行錄製美國作曲家作品以及通俗音樂的計劃。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之後,部份逃出祖國的匈牙利音樂家在海外組成匈牙利愛樂,並與 Mercury 在著名的維也納愛樂廳灌錄雷史畢基「古代的歌曲與舞曲」,成為Mercury銷售量最好的唱片之一。在巴黎和紐約,Mercury為傳奇法國管風琴家杜普瑞 (Marcel Dupré) 錄製法朗克、維多爾與梅湘的作品。接著又在卡內基音樂廳,錄下由曼紐因獨奏,杜拉第指揮明尼亞波利交響樂團協奏的巴爾托克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
大鍵琴家普亞納 (Rafael Puyana) 承續老師蘭櫢芙絲卡 (Wanda Landowska) 的遺志,重振現代人對這種歷史達三世紀樂器的興趣。鋼琴家巴夏爾 (Gina Bachauer) 與拜倫.堅尼斯 (Byron Janis) 把焦點集中在他們所知專長的曲目,包括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最受歡迎的協奏曲與獨奏曲。史達克的良師益友巴爾托克、高大宜與萊納,對其音樂事業、音樂哲學影響甚大。史達克現已不僅被認為是世界項尖的大提琴家之一,同時也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音家之一。
Living Presence 另一項歷史性里程碑,是採用35mm電影膠片錄音技術。法恩會把35mm電影膠片用在 Living Presence 的錄音上,當然是以前為電影音樂錄音的經驗使然。他認為35mm的電影膠片是一項重要突破,它此傳統錄音磁帶更清晰、動態更大、瞬間反應更靈敏,並幾乎沒有磁帶上的嘶聲。 這個新技術對歷史性的『南北戰爭』唱片的錄製提供極佳優勢,「蓋茨堡戰役時代」一段的音樂與戰爭場面的音效,一共錄了九十三軌,最後再混音在一起。Westrex電影錄音設備在一九六一年正式加入 Mercury 的錄音陣容,同年被送往倫敦進行錄音,並於次年遠征莫斯科。
Mercury唱片公司在一九六一年賣給美國飛利浦白熱燈公司的分公司「Consolidated Electronic Industries Corporation」。飛利浦公司是本部設在荷蘭的電器界巨人,原來 Mercury 古典部的成員仍繼續在美國與歐洲兩地錄音,並統籌飛利浦古典音樂在美國發行的業務。一九六一年夏天,飛利浦請 Living Presence 錄音小組使用35mm電影膠片技術,前往倫敦錄製李希特與孔德拉辛指揮倫敦交響樂團的李斯特鋼琴協奏曲,是為購併後在美國發行的首張唱片。(飛利浦的錄音先前以Epic廠牌在美國發行)
威瑪.柯札特在一九五六年出任 Mercury副總裁,由於日久生情,一九五七年與製作人法恩結婚,傳為佳話。她在一九六四年辭去副總裁職位專心持家。柯札特離職以後,古典部監督勞倫靳(Harold Lawrence) 繼任任 Mercury 負責人。一九五八年加入 Mercury 的奧斯道爾 (Clair van Ausdall) 則全權負責飛利浦的業務。法恩仍然繼續擔任 Living Presence 的技術顧問。一九六七年是 Living Presence 的最後一次錄音,樂團是德州聖安東尼交響樂團 (San Antonio Symphony) 與羅梅洛錄製維瓦第與羅德利哥吉他協奏曲。由後來離開Mercury到倫敦交響樂團擔任經理的勞倫斯與艾伯倫玆負責這次錄音。「我們已經把這種錄音技術發展到極限,並對追求再現演奏原音不遺餘力。」柯札特法恩提起 Mercury Living Presence 的錄音哲學時這麼表示。
樂評家弗瑞德 (Richard Freed) 則在紐約時報上總結多年來 Mercury 與合作藝人間的特殊互動關係時說:「如果演奏家們的這些錄音,比一般的錄音室錄音顯得更具生命力、更接近現場效果,可能是音樂家們受到 Mercury 錄音技術生動、並能傳真彰顯詮釋細節的雙重刺激所致。」
Mercury之所以會著手錄製南北戰爭時代的音樂與戰場音效,因緣發生在一九五六年蓋茨堡某家旅館的房間。當時費德利克芬聶爾 (Frederick Fennell) 正以朝聖的心情前往曾經是南北戰爭戰場的蓋茨堡,他在睡前閱讀了史托瑞克 (Storrick) 的「蓋茨堡戰役」。芬聶爾在書上不經意看到一段日記,日記的作者是跟隨李將軍的英國偵察員陸軍少尉弗瑞曼托 (Arthur J. L. Fremantle),他寫道:「當雙方交戰到最高潮時,美國南方的樂隊卻在演奏波卡舞曲和華爾茲。這些音樂聽起來十分新鮮有趣,因為他們用噓聲或是發射砲彈來伴奏。」 看完這篇日記後,芬聶爾從床上跳了起來,披上衣服走到灑滿月光的田野。他想從這塊大地上找出當時南方樂隊演奏的正確位置。當他坐在隆斯垂特將軍 (General Longstreet) 的大砲上時,芬聶爾飛奔的思緒就像和子彈在賽跑:何不使用當時的樂器再演奏南北戰爭時期的音樂呢?
芬聶爾回家後,向伊士曼音樂院 (Eastman School Music) 執行長韓森 (Howard Hanson) 提起這個主意時,韓森對這個計劃也相當感興趣。於是芬聶爾一頭栽進了這項浩大繁複的不朽工程。 首先要做的,就是確認弗瑞曼托在蓋茨堡戰役的第二天到底聽到什麼音樂。芬聶爾在幾個月內翻遍了相關的史書、刊物,或是南北戰爭的研究論文與聯邦政府的軍團記錄。他找到了北卡羅萊納州第二十六軍團樂隊的文件。毫無疑問,這就是弗瑞曼托在日記中所提到的樂隊。
對芬聶爾來說,找出北卡羅萊納州第二十六軍團的音樂所帶給他的挑戰,就像印第安納.瓊斯找尋失落的方舟一樣困難。不出所料,這份文件沒有記載任何樂譜。芬聶爾把他多方搜集得來的結果刊登在 Mercury 的通訊 (Album) 上。不久,一些人開始提供芬聶爾一些當年使用的樂譜。由於許多資料年代久遠,芬聶爾還得仔細校對譜表或是小節線的位置。有些模仿二十六軍團演奏的小型樂隊,還提供給芬聶爾錯誤的資料。與這些難以辨識的資料奮戰過後,芬聶爾終於理出了一點眉目。
芬聶爾找來六位伊士曼管樂團 (Eastman Wind Ensemble) 團員到他的工作室,仔細閱讀並修改他從這些資料上抄下來的四十段曲調後,再把這些曲調錄成帶子。芬聶爾從資料上得知,二十六軍團樂隊的音樂家們都負有雙重任務,這也就是為什樂隊的業餘色彩非常濃厚:「他們在某些特定場合演出,或是在行軍後為士兵們喝采鼓舞士氣。平常則在野戰醫院擔任醫護兵。」
芬聶爾曾經與新漢普郡第三軍團 (Third New Hampshire Regiment) 聯合樂隊的成員相處過一段時間。聯邦政府軍在戰爭期間攻下 Hilton Head 後,就在南卡羅萊納防禦區設置要塞,由這個成立於一八六一年的軍團負責駐守在這個地方。
與陳年的歷史資料、手稿「激戰」後,芬聶爾開始尋找南北戰爭時期樂隊所使用的銅管樂器。這方面的資料大部份來自私人的博物館或是個人收藏。他們的號角經過特別設計,喇叭口朝後方是為了方便聲音傳送給後面行軍的士兵。
這種喇叭口高過肩膀的銅管樂器,後來發展成有旋轉式活塞的裝置。德、奧兩國在十九世紀初也製造過這種樂器。美國銅管樂器製造家道斯渥茨 (Allen Dodsworth) 在一八三八年模仿歐洲的設計,並且發明了一系列旋轉活塞的的銅管樂器。這種樂器的喇叭口從吹奏人的左肩延伸到背後。南北戰爭期間,南北雙方在遊行時都使用這種樂器。
芬聶爾在樂器的還原上有少許讓步。一八六○年的豎笛和一九六○年的豎笛在聲音上有一點不同,但是芬聶爾選擇了現代的豎笛。而某些吹奏技巧對橫笛來說過於吃力,所以他使用短笛來取代。重現古樂器的工作就交給伊士曼管樂集的法國號手。
除了音樂以外,南方樂隊與聯邦樂隊間還是有顯著的不同。北卡羅萊納州第二十六軍團樂隊的編制只有幾隻喇叭口高過肩膀的銅管樂器,並沒有一般軍樂隊所使用的鼓。聯邦政府的大型樂隊編制則包括三隻短笛、四隻豎笛、十七隻喇叭口高過肩膀的銅管,大鼓、小鼓各一。芬聶爾堅決主張不可使用鈸,因為所有關於南北戰爭時代的書籍,或是當時的照片都完全沒有提到這種樂器。
北卡羅萊納州第二十六軍團樂隊的音樂雖然平淡無奇,卻不失純真自然。由美國南方的小樂團演奏時,更能使人感受到那一份清爽感。這種「驚豔』的感覺,絕不遜於由好萊塢大樂團演奏的管弦樂改編版。這張使用 Mercury Living Presence 技術錄音的唱片,所激動的聽者情緒遠超過上百人大樂團的演奏。 芬聶爾還發現到一件有趣的事情:南方政府的「頌歌」(相當於國歌)的作者是北方人。這首歌曲是作者艾密特(Daniel Decatur Emmett) 為紐約一個流動樂隊所寫,原來的曲名是「The Grand Opening Number」。南方政府利用這首歌曲來鼓舞人民,並把這首歌改編成較抒情的風格。北卡羅萊納州第二十六軍團樂隊經常演奏的曲目大部份是頌歌、進行曲、感傷情調的民謠以及快速的進行曲。
聯邦樂隊的演出曲目則包羅萬象,少部份是自己創作的,如:「Hail to the Chief」、「Hail Columbia」、「Cape May Polka」。大部份的樂曲都來自歐洲,包括歌劇什錦歌,如韋伯「魔彈射手」、威爾第「假面舞會」,以及約翰.史特勞斯的圓舞曲等。
除了重建南北戰爭時期之聲以外,芬聶爾還全力尋找這時期為短笛、鼓與騎兵號角所寫的進行曲。芬聶爾一開始就向Mercury提出這項計劃,之後四年,也就是一九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芬聶爾與錄音小組開始整合這四年來所蒐集到的資料,由伊士曼管樂團在位於羅契斯特的伊士曼劇院,使用當時的樂器進行錄音工作。 這次古怪複雜的錄音工程應該可以在錄音史上留名!芬聶爾把這幢磚造劇院的樂團席栘走,並且排出錄音史上最奇怪的團位置。吹奏牧笛的團員面對聽眾坐在突出於幕前的舞台,其他團員則隨便坐在舞台各個一個角落,有些演奏號口朝後喇叭的團員甚至必須背對指揮!芬聶爾很輕鬆就解決這個問題:他到距離錄音現場最近的汽車用品專賣店買了七個照後鏡。
喇叭口高於肩膀的銅管樂器由法國號樂手吹奏。他們背對指揮,喇叭口朝向舞台前方的麥克風。兩名打擊樂手則面對面站在舞台的兩側。芬聶爾戲稱自己這次的編排是「邪門歪道」。所有樂曲都在一九六○年十二月完成,但是整個計劃的重點卻在蓋茨堡完成。為了在錄音中重現拿破崙青銅加農砲、威靈頓舊�"B槍等南北戰爭時期武器,Mercury的工作夥伴決定加錄一段音效。在美國西點軍校博物館館長史托 (Gerald C. Stowe) 的協助下,Mercury匯集了一段讓人印象深刻的武器大展。
所有武器的聲響都以半英寸三軌的錄音設備錄製在35mm的磁帶上。加農砲設在戰場位置較低的地方,由工程師法恩 (Bob Fine) 以車載運錄音器材在三百碼以外的安全距離錄音。三個擴音器則面對發射線,分別掛在長十五英呎的竿子上。紐澤西輕大砲聯隊部份隊員在加農砲口裝填大量用水浸泡過後的報紙充當砲彈,並把砲口朝向不遠處的麥克風。
錄音器材的大部份電力以特殊線路從公路上的卡車傳送過來。電纜分佈在戰場各個角落;
麥克風掛在釣魚竿、高的木柱,或是懸掛在一些特別設計過的汽球上,錄下四門由生鐵製成、重約十磅的加農砲,兩門十二磅重的拿破崙青銅曲射砲等武器,齊發或個別發射的聲音。
除了大砲連續發射的聲音以外,Mercury還錄下馬蹄聲、彈藥搬運車轟隆轟隆的聲音、馬嘶聲、騎兵隊的呼喊聲、炊具 碰撞聲,以及發射子彈、左輪手槍退出彈殼、來福槍上的刺刀、連發�"蚨硅j音效。每一種武器都在音效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整個過程都在麥克風下方負責錄音的工程師法恩說:「我從錄音帶上再次聽到這些音效時,各個武器的聲音都非常清楚,涇渭分明。沒有任何一種武器的音效被其他武器掩蓋過去。」 重新編排音樂以及蓋茨堡戰役音效的後置作業非常辛苦。最後選用其中一千五百多發南北戰爭時期武器的音效與音樂,利用九十三段35mm的磁帶合成為一部 「音效記錄片」。Mercury以豪華包裝發行兩張一套的「南北戰爭音樂與戰場音效」。兩張唱片分別是兩種顏色,一張代表南方政府,一張代表北方政府。另外還有一本附插圖的精美小冊子,除了一篇由芬聶爾親自撰寫,文長超八干字介紹錄音的源起與過程的文章以外,還有蓋茨堡戰役的遺址,以及這張唱片所使用的樂器及武器等照片。
經過四年籌劃,Mercury Living Presence於一九六二年春天在莫斯科寫下錄音史新的一頁。美國錄音小組的工程師與職員有史以來第一次獲准進入蘇聯進行錄音工作。在這值得紀念的十天當中,Mercury的工作夥伴與重達四噸半的先進器材,錄下了蘇聯境內首屈一指樂團及音樂家的演奏實況,長度差不多等於五張唱片。並邀請美籍鋼琴家拜倫堅尼斯 (Byron Janis) 參與演出。這是堅尼斯第二次應邀在俄國境內巡迴演出。
內容註
Piano concerto in A minor, op. 54 ; Arabeske, op. 18 / Robert Schumann. Piano concerto no. 1 in B-flat minor, op. 23 / Peter I. Tchaikovs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