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狐仙故事
- 題名: 狐仙故事 = Fox tales / 國立國光劇團場.
- 其他作者:
- 其他題名:
- Fox tales.
- 出版: 台北市 : 國立國光劇團場 民99[2010].
- URL:
https://serv.npac-ntch.org/DVD/4A/DV04136.htm
- 一般註:2009年10月16, 17, 18日城市舞台演出. DV04136為公播版 DVD.
- 演出者註:陳美蘭 ; 朱勝麗 ; 盛鑑 ; 陳清河 ; 羅慎貞 ; 王耀星 ; 張光鳴 ; 王逸蛟 ; 謝冠生 ; 劉海苑 ; 劉稀榮 ; 許孝存 ; 蔣孟純 ; 張家麟 ; 尹來有 ; 劉嘉玉 ; 鄒慈愛 ; 陳長燕 ; 劉珈后 ; 孫元城 ; 陳富國 ; 陳元鴻 ; 陳忞鴻 ; 傳威瀚 ; 戴心怡, 主演. 柯基良, 監製 ; 陳兆虎, 製作人 ; 王安祈, 藝術總監 ; 趙雪君, 編劇 ; 李小平, 導演 ; 李超, 唱腔作曲 ; 李哲藝, 編曲配器 ; 傅寯, 舞台設計 ; 任懷民, 燈光設計 ; 蔡毓芬, 服裝設計 ; 劉嘉玉, 編舞 ; 許培鴻, 平面攝影 ; 鄭司雅, 平面設計.
-
讀者標籤:
- 系統號: 005102673 | 機讀編目格式
館藏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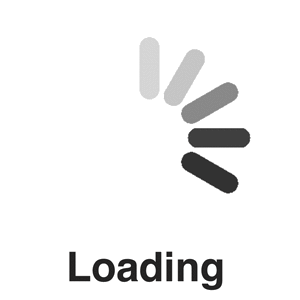
摘自 國立國光劇團網站
封三娘在山中誤觸陷阱,白狐所變的男子替她解圍,三娘對白狐產生了愛慕之心。白狐卻因為過往而猶豫不決——他曾經有過一段不容於世人的人、妖之戀。最後決定露出狐妖的原形嚇走三娘,從此分手。
三娘轉世為也娜,被一群妖怪撫養長大。十八歲遇見親生父母,妖怪將也娜還給她的父母。也娜不快樂,父親也為她訂下一門親事,眼見得也娜日益萎頓,母親希望妖怪們在也娜出嫁當天搶親。
五十年後,妖怪們欲要冒險為她取來不老不死的仙草,也娜不願意連累親人,悄然離去,來到三娘曾居住的山裡,遇見了前世愛慕的白狐。白狐每日與年老的也娜作伴,直到臨終。
摘自 聯合報 / 王安祈
我自己在三十歲開始編劇時,就是以我這一世代的思維和京劇傳統相抗衡──也可以說相承接。而二十五年後,動漫與網路世代的思維掌控全世界,京劇若能代代有新編劇說新故事,才能扣緊時代脈搏……
《狐仙故事》,靈感得自日本漫畫。把京劇和漫畫連上關係,不是噱頭,反映的是新世代閱讀習慣、審美偏好以及思維方式的改變。
「視覺閱讀」對劇場的影響顯著,戲劇的設計群原本以舞台、燈光、服裝為主,近年來多了一位「影像設計」,一開始只偶然出現,後來逐漸普遍,舞台上除了演員演戲之外,布景道具愈來愈重要,多媒體投影更是新趨勢。此一現象的形成,科技進步固然是基礎,觀演雙方接收習慣、思維模式的改變更是內在原因。
傳統戲曲受到「視覺閱讀」的影響更值得探索。新編戲曲不見得都在台上投射影像,但敘事傳統則有明顯改變。幾百年來戲曲說故事的方式多受說唱藝術影響,原原本本、娓娓道來,即使有多條線索,也「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分頭敘述,到必要時再交織穿插或兩相對應;長篇故事可以選粹摘錦,挑出一、二折子單演,為了幫助觀眾瞭解前後情節,偶爾會做些序曲、尾聲、倒敘、插話的變化,但功能只在修補聯綴,並無創新敘事結構的意圖。大抵而言,「載歌載舞、抒情造境」始終是戲曲的主體。
而新世代說故事的習慣卻不同了。我和《狐仙故事》編劇趙雪君師生二人即是兩個世代代表。我的童年讀物是章回小說,雪君則是標準動漫網路世代。我構思劇情時首先有「場」的概念,整個故事在腦海中先切成幾個段落,高下起伏輕重緩急,胸中自有定數;而雪君說故事卻神光離合,三百年前和五十年後的事可以在三秒鐘內同台並置,情節的銜接轉折未必用語言一一細說,有時一個輕紗蒙面、相互追逐的畫面即可傳遞一切。很多情節要看到後來才恍然大悟,採用的卻又不是什麼補敘倒述。
漫畫的分格,導致思維的閃耀跳盪,看似斷裂,實則內在情絲牽綿,自成脈絡。狐仙故事要的正是這個,靈動、詭譎、飄逸、閃爍、奇幻。
漫畫分格的思考和電影鏡頭正可交互運作,這樣的敘事結構惹得正迷上電影的劇場導演李小平玩性大發,摩拳擦掌準備大發揮一番。而小平是專業京劇演員出身,不可能捨棄戲曲「合歌舞演故事」的本體,他知道未必真的要用影像設計,京劇演員身形姿態本身就是絕美視覺。只不過傳統戲直接以「下腰」「臥魚」代表啣杯醉步、倒臥花叢,新戲則可水袖一轉、隨即定格亮相,一動一靜之間,電影畫面就在舞台上凝塑而成。
編唱腔的李超老師可苦了,我畫了好幾張人物關係表格對李老師解說劇本,第三遍讀完,李老師重重拋下本子,長嘆一聲,說道:「《 穆桂英掛帥》真叫好編,一場是一場,唱腔多容易成套安置啊。眼下這劇本兒,線頭多,零零散散,才起一勢頭,我準備要下『反二黃』了,翻過一頁,怎的忽又斷了線? 這唱腔怎麼編哪?西皮二黃都成不了套,只能是一首一首的歌兒!」
「中國京劇院」出身的李老師實在不習慣,而我聽著他的抱怨,不免私心竊喜,因為我知道這戲的唱腔絕對不會被傳統套式框住。
京劇藝術講究氣派大方,但狐仙故事不適合,要的就是瞬間變滅,無論情節或唱腔。
李老師要我把劇本改一改,我可不想動手,因為我從雪君筆下讀出了屬於這時代的氣息。
年輕演員可以打造舞台的青春光采,新世代編劇的分格與分鏡思維,則能創造新的敘事風格。我一直推動的「戲曲現代化」,焦點就在故事的情感思想,以及說故事的技法。我自己在三十歲開始編劇時,就是以我這一世代的思維和京劇傳統相抗衡──也可以說相承接。而二十五年後,動漫與網路世代的思維掌控全世界,京劇若能代代有新編劇說新故事,才能扣緊時代脈搏。
雪君這幾年以《三個人兒兩盞燈》和《金鎖記》崛起劇壇令人驚豔,而這兩部新編京劇都是我們師生共同合作,唱詞大部分出自我手,所以京劇的本體仍很穩固。但《狐仙故事》是雪君獨立完成的第一部京劇劇本,我刻意只盡一個老師的本分,專挑毛病,讓她自己修改,我儘量不動手,因為我喜歡年輕口吻所傾訴的新鮮故事。
妙的是劇本從構思到完稿正和雪君從訂婚到結婚步調完全一致,兩次大修改還剛巧遇上蜜月。第一度蜜月在北京,新郎獨自從鳥巢、水立方逛到老胡同、四合院,新娘獨坐旅館對著電腦苦思修改。完稿伊媚兒一寄出,即趕赴機場返台。回家後心有未甘,定下二度蜜月行程,選擇的恰是狐妖故事靈感發源地日本。誰知登機前竟又接到我發回再修的指令,新郎新娘只有帶著劇本漫步京都古寺,追尋著漫畫裡的妖氛足跡。
其實此劇和日本漫畫的關聯只在發想時的靈光一閃。最初我想弄一部鬼狐妖怪的新戲,以便京劇演員好好發揮身段武功。和雪君、正平約在「西雅圖」聊劇本題材,先從《聊齋》裡找,不料最觸動我的竟是雪君隨口提及的《除妖怪譚》漫畫,我當下察覺其中有戲大可發揮,於是以此為起點,東一句西一句任意發展,故事居然大體成形。我們談的當然不只是劇情,焦點更在人與異類相愛的各種可能。情感思想的厚度,是我最堅持的。
而雪君的情愛觀與四年前《三個人兒兩盞燈》竟已不同,編那部新戲時她還沒談戀愛,戲裡寂寞女子將一生情愛化作小詩一首,遙寄縹緲的彼岸,聊作依托;而今與愛情已然相遇的雪君,卻領悟了「割捨」才是真愛,狐狸上下百年忽作男、忽化女,為的竟是閃躲避藏以成全愛人幸福。作為老師,其實我很不捨,新婚蜜月談什麼「放手、割捨」?好在戲中人與狐愈閃避愈貼近,情思糾纏竟似三生石上情緣前訂,愈到結尾處情感愈濃,惹得我幾番掩卷不忍觀。
台灣新娘以日本漫畫為起點編織的情愛故事,對天地是否「大有容」提出質疑,情思深沉,結構卻輕盈,這正是我所期待的。我非常不喜歡缺少情感內涵只玩弄技巧的輕薄小品,也非常不喜歡只重視氣派卻沒有細膩情感的大而無當大製作,姓不姓「京」我倒不在意,只要動人必是好戲,何況一代有一代的文學藝術,京劇未必永遠定於一格,台灣新崛起的新編劇,說不定能創造京劇自身的新傳統呢。